作者🤟🏿:杨庆峰 发布时间🧏🏼♂️🏇🏼:2023-01-18 来源:数忆苑+收藏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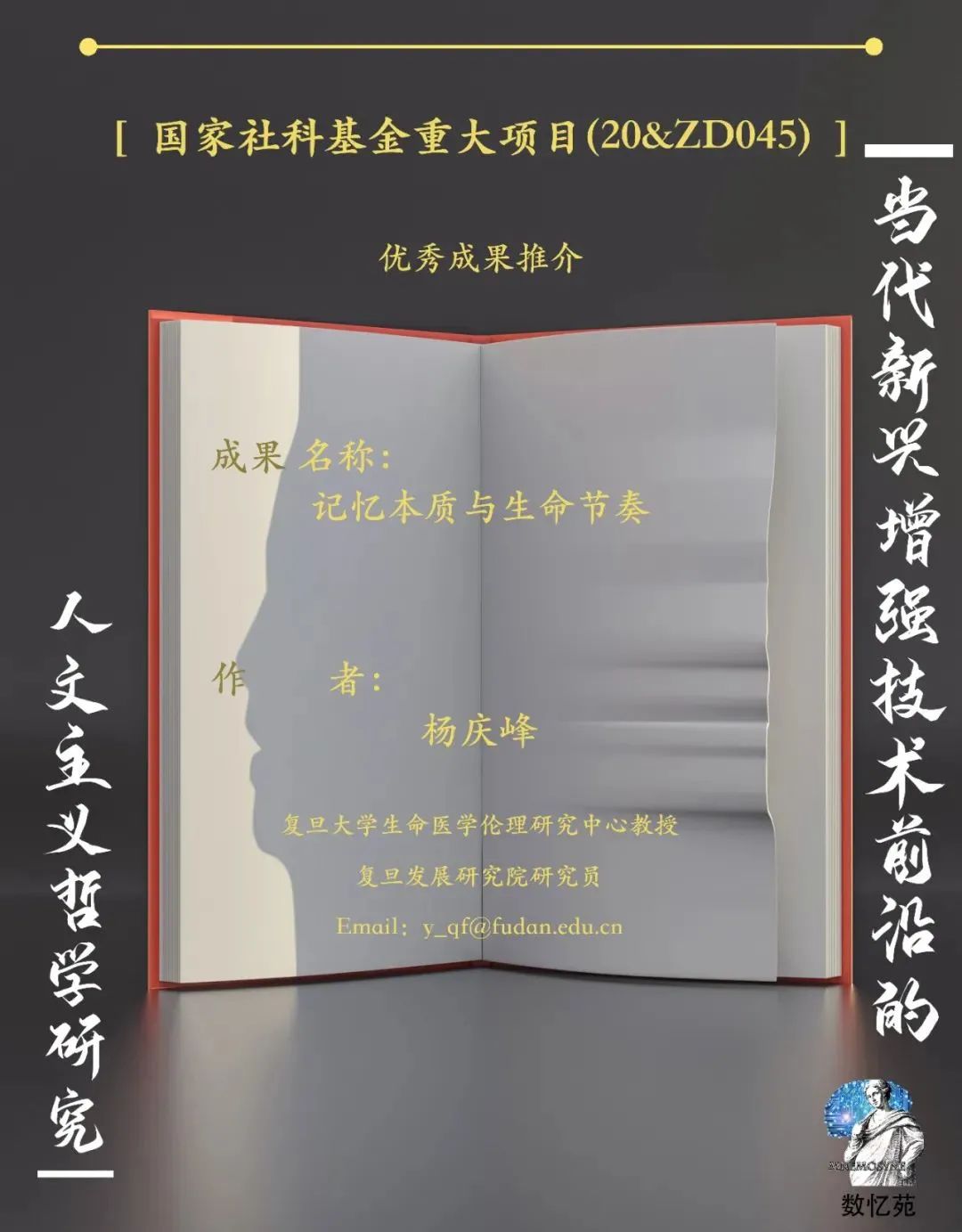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杨庆峰
富达平台研究员
富达注册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
Email:y_qf@fudan.edu.cn
正文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历史、记忆与遗忘》的末尾用了这样一句话结尾🌋⚉。“在记忆和遗忘之下,是生命。书写生命却是另一种历史。永未完成🫸🏻。”这句话说明了记忆与生命的蔽與潔碧的關係。就他本人来说🧑🏽🦱,他从记忆入手,通达历史与生命👐,最后用遗忘结束正本著作👨🏼🔬。这个逻辑是完整的,但是他也留下了一个问题🦹,愉快的记忆对于生命而言的意义👩🏿🦲。在各种增强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光遗传技术可以做到记忆的删除、植入与激活🙆🏿♀️。在科学的实践活动中✧,是对痛苦的记忆做的各种各样的删除和植入。于是📄,愉快的记忆与痛苦的记忆在我们这个时代相遇,构成了我们记忆实践过程中的一个有趣抉择,让我们对追问记忆与生命有了新的可能性🕠。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记忆理解为意识现象。在这种理解中👩⚕️,记忆是一种不同于知觉的现象,缺乏足够的自明性、表达为知觉的滞留;也有的理解将记忆看作是身体现象,在这种理解中,记忆是一种身体行为,比如一旦学会骑自行车,就不会忘记。这被称为程序记忆。还有一种对食物味道记忆👨🏽🚀,也属于此类。当远离家乡的游子品尝到故乡的美食时,家乡的味道会萦绕包围他,食物的滋味会满足于他渴望已久而显得空虚的胃👉🏿。与此相呼应🔴,法国作家普罗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关于“玛德琳娜”小蛋糕和配的那杯茶充分表达了这种味觉记忆。这两种理解中,记忆呈现为意识或者身体机能🩼,并且贯穿在哲学史中𓀋👱🏻♀️。

在学术界中👨🏻🦲🤦🏼♀️,记忆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其中神经科学与哲学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决定了我们对记忆的认识。二十世纪的神经科学为我们贡献了两种记忆观点。一种是痕迹说,认为记忆是神经元的链接。这种观点在二十世纪中叶占着统治地位。但是,最近一种适应说开始兴起。这种观点认为记忆是一种适应现象,生物体对不同层面的系统对于过去的刺激的适应。这种观点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在哲学中,对记忆的理解更加突出了记忆对于人的意义。从灵魂机能、意识现象都表明了记忆与灵魂和意识的关系🔢。但是,记忆的科学理解没有触及记忆的时间本质🙌🏼✣,没有体现过去概念,在其看来,记忆更多表现为与信息内容有关的活动。记忆的哲学理解通过时间性把我们带入到记忆与生命过去的关联。
在深入说明二者的关联之前👌🏿,我们需要提及20世纪60年代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关联🌎。这个时期,科学家开始关心心理学对于记忆理解的帮助🚿。在这之前记忆的生理学对记忆的机制给予了物质化解释♜;而随后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则对同样的机制问题给予了心理学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突出了信息的编码过程。如今,我们又面对神经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在一般哲学看来,记忆是一种能力。因此在这一基础上,科学展开一种记忆实践探索🤵🏽👨🦯➡️。随着神经技术、医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从神经技术角度看来🤴🏼,光遗传技术被看作是打开大脑的钥匙,科学家利用这种技术激活或者抑制痛苦记忆。这种研究直接验证了哲学上提出的记忆痕迹概念。而记忆痕迹很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戒指比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念让删除记忆🥛、修改记忆和植入记忆成为可能。这种改造性的记忆实践不断冲击着人们对记忆的理解。比如什么样的记忆可以被删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见到三种疑惑🩰。第一种是记忆是生命同一性的基础。如果这样删除记忆就会影响到人的个体认同。事实上,这样的担忧也有根据🧍♀️👰🏿。在记忆研究史上H.M的遭遇就表明:记忆删除会产生记忆认同的问题。做过手术的H.M备受困扰📓,永远生活在“当下”。第二种是记忆是生命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这样,记忆删除必然会使得生命变得残缺不齐。第三种是好的记忆与坏的记忆的区分或者我们称之为愉快的记忆和痛苦的记忆区分。坏的记忆会影响生命发展和生活质量✋🏼。我们曾经听到很多PTSD案例➔、听到一些超忆病人的困惑。这些记忆都是坏的记忆🧑🏼⚖️,或者是由于过去的伤害而形成的记忆,或者是过量无用的记忆影响到当下的决策。如此,面对这些记忆对其进行删除,可以获得伦理的辩护。但是对于愉快的记忆,我们会发现,碰触到这类记忆会对生命本身产生危害。

面对这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辩护意见🧑🏿✈️🤨。针对第一种记忆是生命同一性的观点*️⃣,目前关于记忆分类的理解并无助于我们理解记忆与生命同一性的关联。在心理学的记忆分类中,有短期记忆和短期记忆的区分♠️,也有语义记忆、情景记忆和程序记忆的区分。这些记忆很难确立起和生命同一性的关系。何种记忆会形成生命同一性?在一般情况下,我会把当下和过去联接起来🙇♂️,并且完全符合起来🦶🏻👏🏿,生命不会造成混乱。比如今天的我和过去的我是否是同一个,就属于同一类问题。针对第二种观点记忆是生命构成物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我们更多是从经验角度来看的结果。人生所受的磨难都会化为经历而成为生命的养料😾🟢。而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是经验的一种累积和升华。这很显然不是记忆的一种规定性😧🫦。很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待填补的鸿沟🤴🏿。针对第三种观点愉快的记忆和痛苦的记忆。这是一个很难划分的问题,首先记忆的性质是一个不同角度的看法。如果角度改变,势必导致记忆性质的看法。其次是记忆的愉快与痛苦是感受问题。主体的感受很重要,有助于自己成长的记忆即便开始是痛苦的🧨,也会演变为愉快的👨🏽🎤。此外,愉快的记忆会更加愉快👊🏊🏽♀️,被牢牢记忆。还有记忆的愉快与痛苦是根据某个标准评价的结果🤺。标准不同🎊,势必导致某种记忆的变化🕵🏻🌋。这与角度的看法略有不同。
在增强技术的语境中🥏,记忆被限定在能力上,同时也建立在可以区分性质的基础之上。然而这种理解的局限还是非常明显的。记忆被当作一种能力,可以进行不同等级的提升。但是在这种理解之中,却忽略了记忆作为过去场景构建的规定性🐦🔥。然而,在这种观点中👨🏻🦯,有着心理学的支持。情景记忆就是这些场景的再现🧢。很有意思的🤴🏿,关于过去场景的构建在技术上也成为了可能。利用脑机接口进行记忆重演,利用Dormio(一种俘梦系统)进行记忆场景的捕捉,这是一种利用可穿戴设备再现回忆的方式。

但是,对记忆的理解还是需要超越记忆能力的限制🙅🏽♀️。我们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着对记忆的改造✡️,而我们进一步需要追问一个问题:改变的是什么⚠️?从能力说的角度来看🤯,是对一种保持信息和提取信息能力的改变👨🏻🦯➡️。但是这种讨论并没有触及到生命本身🧔🏻,尤其是生命节奏🔒。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一种流变和绵延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流变和绵延中有着某种固有的节奏。一年的四季变化、一天的黑夜白天变化就是自然界流变中的节奏。如果我们面对音乐,就会这种节奏有更为准确的把握。一段音乐是按照某种特定的节奏行进的东西。对于生命本身来说🍓,人的活动构成了这些节奏的内容🎼。当我们理解了这种节奏🔚,对生命本身的把握就会更加切实。生命的流动是按照节奏进行的,一旦生命的节奏被打乱,就会陷入紊乱。也就会进入疾病状态中。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记忆是什么?记忆就会成为生命的滞留物🆚。在这种滞留物中,不仅有内容的滞留、而且还是节奏的滞留🤱。记忆就是如此,此外,这种滞留表现为生命体受到外界不同的刺激而从生命节奏本身表现出的适应。从内容来说,受到刺激之后🧐,容易留下痕迹2️⃣,从节奏来说,受到刺激之后👩🏽🎨,节奏能够有效保持自身。这样的解释会使得我们对记忆的理解超越记忆能力说的限制,从而指向生命本身🚒。
如果我们从利科的角度来看🫃🏽,会加深对生命与记忆的理解🥝。利科曾经指出🛖,历史、遗忘与记忆之下是生命🫥。这种描述性的观点并没有指出历史与生命的节奏🧗🏼♀️👂🏼,从节奏角度看📥,历史的节奏和生命的节奏有着同一性。我们要格外强调这种隐含在生命之中的节奏🌲。这种节奏并不是生命体静态的结构,而是隐藏在流动之中可触摸、可变形的东西📚。我们最多可以把节奏看作涌向未来的结构的复制品🧘🏿♀️👩💼。因此❇️,当我们从生命节奏出发🛌,对记忆及其改造实践会有一个新的变化。记忆的改变并非仅仅是能力的提升,而是对生命节奏的触发⏬。通过这种观点👨🏼⚕️,我们对愉快的记忆和痛苦的记忆有着新的理解👐🏼。愉快的记忆是指有助于生命节奏形成和行进的东西🤦🏽,这是基于过去的一种变化🤯。而痛苦的记忆是造成生命节奏紊乱的东西💇♀️🏣,而且难以回复的原初状态的东西👨👩👧。如此,记忆删除就会使得生命找回自身节奏的一种有效手段。